兰清竹韵
刘孟浩博客-刘孟浩个人网站
当前位置:首页 » 书画频道_书画艺术_书画作品_书画展_书画家_文人画_书画培训_书画装裱 » 正文
-
很多人说,自己已经学了十年二十年,要让他全部丢掉就心疼,他那些东西在当地别人要的就是那几招,扔掉了这两招还怎么混?我对很多前来学习的学员们在交流的时候说,年龄不饶人。也就是说我们年龄越长,你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越少,反过来说,你剩下的时间越少,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使命感就越强呢?他如果二十岁,耽误十年也才三十岁,你五十岁耽误十年就六十岁了,你就应该比他更要讲究科学性,你要更有勇气来否定自我,彻底丢掉你以前阻碍你发展的东西。
如果我们的教学给你提供了更捷径、更本质、更能提升自己的方法,你还有什么包袱舍不得扔呢?越大年龄的人越要扔,越大年龄的人越要改变,因为你输不起,也耽误不起,这么多年的平庸已经证明你那段是无用的,是不能成就你的。你在那儿转了三十年还没有上到二楼,还在留恋你那一套吗?别人学了三十年都成全国名家了,都可以进入书法史了,你搞了三十年原地踏步,还舍不得你那一套,还要修修补补吗?你想把你的手扶拖拉机改造成奔驰,除了立马推倒你的厂,引进奔驰的技术,还有其他路吗?学习就是这样,有了先进的立马扔掉既往的,全盘否定,一点不剩你才有可能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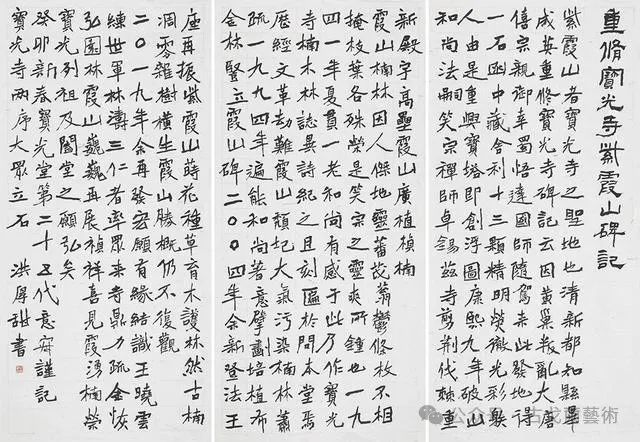
为什么陈振濂老师要让我来讲“书法学习科学的临帖和方法”这种很本质、很原始、很宏观的这种东西呢?我从基层走出来的,当时学书法想写到我们县的最好,现在回头一看,写到市最好都没用,但是人生就是要靠这样的小目标前行。从一九八零年到两千年这之间,我做了多少事情?九二年我开始把以前所有的东西重新反省,到杭州来拜陈振濂老师为师,到陈老师工作室来学习,全部从头推倒重来。九四年开始跟陈老师在全国搞教学,一直到现在不间断,只要有陈老师的班,就有我去参加教学,而且我还在陈老师的工作室学习。
我们要完成一个最基层的普通青年个体到一个专业领域里专家的过渡要付出非常艰辛的努力。学习到了一定时期就是自己来把握自己,也就是我们对书法史的观照方法就决定我们最后的成果和状态,就要不断的追问我们的学习科学吗?我们的临帖方法正确吗?在一楼是正确的,在二楼还正确吗?第一阶段是正确的,二阶段还实用吗?
我说了,在楷书这个领域里面,宋代这么牛的朝代,要选三个人都很难。现在我们看到的米芾的楷书就是小楷《向太后挽词》,有这样一个东西就足矣,大家看我写《倪宽赞》的技巧,有相当多的成分跟《向太后挽词》相近。可能有人问老师你为什么写褚遂良要去学米芾呢?大家要知道,米芾是学褚遂良出来的,也就是说米芾有相当大的技术成分是从褚遂良那儿转化过来的,甚至于我们现在有相当的研究资料表明,褚遂良的《大字阴符经》就是米芾的写本。以我三十多年书法研究的积累和感觉来看,说它是米芾写的,也真还能信,我也愿意信,因为我横着看过去在书法史上,米芾之后就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个技术层面上去。
所以说我们有了宏观的视野,我们从米芾只有几行字的《向太后挽词》里面一下子就能找到褚遂良技术动作的对应点。写颜真卿又要去找谁呢?你去把黄山谷的行楷书拿来一看,《松风阁》的那些技术直接拿去解读《勤礼碑》!你不要就颜真卿的这个帖去写这个帖,他晚年的《自书告身帖》都没有你去解读黄山谷来的直接。黄山谷写草书就是篆籀笔法,就是篆书的线条,他写楷书也是篆籀笔意,你拿去就搞定颜真卿。我们谁会觉得黄山谷写的行楷书是僵化的呢?它书写性强不强?强的很。转化厚不厚?厚的很。线条饱不饱满?饱满的很。直接拿去搞定颜真卿。
我说了研究苏东坡,对应的不是唐代,直接是汉魏的东西,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再来研究临帖方法。你去解读书法史的时候,如果眼睛里面只盯着一个点,那你到老也还是那一个点。我们是一个面,一个立体的纵横,学历史不是你记住他干了什么东西,而是他的行为在整个历史中的一个价值存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这样来观照书法史,和我们只看见一个点、只看见一个人、只看见一个帖会一样吗?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点上的生发都会为我们的整个书法家个体意识的培养、能力的塑造和整个知识的构架都要起相当本质的作用。
本文链接:https://www.liumenghao.com/shuhua/8694.html
-
洪厚甜 | 如何科学的观照书法史?
492 人参与 2024年03月30日 20:45 分类 : 书画频道_书画艺术_书画作品_书画展_书画家_文人画_书画培训_书画装裱 评论
- 2024-06-25 17:36洪厚甜:从书法艺术拓开的综合人文素养(五)
- 2024-04-01 20:29净堂示法:史观、意志与精进之道
- 2024-06-03 14:36洪厚甜:从书法艺术拓开的综合人文素养(三)
- 2024-04-25 19:35洪厚甜:怎样才能把楷书做好
- 2024-08-20 21:00洪厚甜:从书法艺术拓开的综合人文素养(八)
- 2024-06-13 16:15洪厚甜:从书法艺术拓开的综合人文素养(四)
- 2024-04-25 18:54洪厚甜:师迹?师心?一一从书法学习的程序设计说开去
- 2024-04-01 21:07楷书的临摹和创作(二) | 国家画院洪厚甜书法公开课
- 2024-04-25 18:47洪厚甜:探本究源一一再谈临帖中的几个要点
- 2024-04-06 15:01洪厚甜 | 草书学习探径(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