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清竹韵
刘孟浩博客-刘孟浩个人网站
当前位置:首页 » 国学大师_国学经典_国学教育_国学经典名句 » 正文
-
《礼记》是战国末至汉初儒家学者论述“礼”的著作汇编,其中西汉戴圣编辑49篇,称《小戴礼记》,为后世所通行。《礼记》一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史料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其中不少内容与教育密切相联,还有一些集中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著作,这些论著对中国封建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就教育理论阐述的集中性而言,首推《大学》、《中庸》和《学记》等。
《大学》中的教育思想
《大学》是儒家学者论述“大学之道”的一篇论文,它着重阐述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步骤,提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政治、道德教育的纲领和程序。
《大学》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称为“三纲领”。意思是:将美好的道德发扬光大,使民众面貌日新,达到最高的善的境界。第一条重在修己,第二条重在治人,第三条是最终目标,这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最明确的概述。
为实现大学教育的三个目标,《大学》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步骤,朱熹称为“八条目”。《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八条的核心是修身,“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前四条体现修身的过程,从接触事物开始,获得正确的知识和认识。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调整和净化自己的思想观念,树立坚定的志向和意志。最终使内心达到纯正的境界。后四条体现修身的成果,由自身,到家庭,再到一个国家,再到全天下。修、齐、治、平是所有正统儒家士人努力的共同目标。八条目前后相续,逐个递进而又相互联系,体现了过程与效果的统一。
格物、致知被视为“为学入手”或“大学始教”,实际上就是学习、领会与伦理道德有关的事物和知识,属于道德认识的阶段。诚意、正心是内心修养过程,着眼于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养成。后四条则是道德行为的建立和扩展。首先是自身完善,即修身。齐家是从修身自然引出的,因“身修,则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于家者也” 。可见,齐家是一个施教过程,即通过个人的修身来完善家族内部的关系。而且,齐家也是治国的基础,如果家家都做到了孝、悌、慈,也就达到了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了,因此,治国不过是齐家的扩大和深化,而平天下又不过是治国的扩大,其基本精神是一贯的。这样,个人的学习、教人、施政等几个方面自然地联系、迁移和发展,成为一个整体。
《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从于封建道德和政治,因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宋以后,被收入《四书》,成为封建教育的基本教科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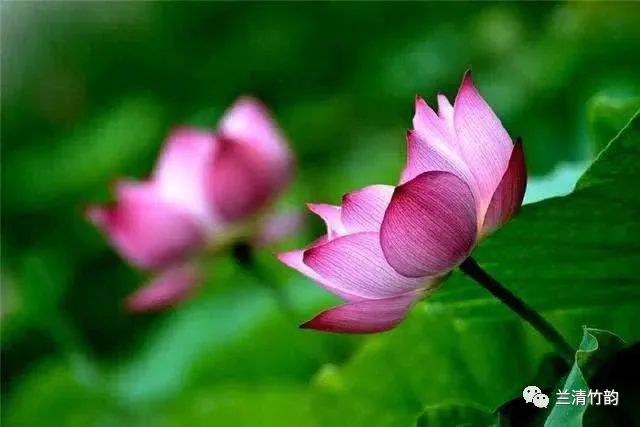
《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中庸》是论述个人修行的一篇哲理性极强的论文。首先,它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与作用。《中庸》一开头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是继承思孟学派“性善论”的思想。意思是说,上天所赐予的称作“性”,顺应和发扬这种本性称作“道”,修明和推广这个道,就称做“教”。也就是说,教育即修道,而教育的作用则在于“率性”,尽量把天赋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体现出来。其实本无什么天命,所谓天命,都是统治者及其御用学者杜撰出来的,用以震慑和愚弄民众,所以这种教育本质论既是神秘主义的,又是专制主义的。
《中庸》还阐述了学习的过程,这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个步骤。“博学”就是广泛的学习,“审问”即对博学中的内容详尽设问置疑,“慎思”即对审问的内容谨慎思考,“明辨”即通过慎思而明辨真伪是非,“笃行”即将明辨的结论付诸切实的实行。这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学习和修身方法,包括了学、问、思、辨、行等几个主要环节。
对于教育途径,《中庸》认为人可以从两条途径得到完善,一是发掘人的内在天性,达到对外部世界的体认,这就“自诚明,谓之性”,或称“尊德性”。二是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求知,以达到人的内在本性的发扬,这就是“自明诚,谓之教”,或称“道问学”。意思是说,学习和教育的实现需要有人性的依据,故要尊重德性,发扬自己先天的善性。同时,人性的完善又要依赖于学习和教育,故要注重后天的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中庸》认为这两条途径是相依并进,相辅相成的。
“诚”与“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教育途径论后被宋明理学家发挥,并以此为标准,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来源:《中国教育史》
本文链接:https://www.liumenghao.com/guoxue/3240.html
-
《大学》《中庸》中的教育思想
1659 人参与 2020年12月18日 14:57 分类 : 国学大师_国学经典_国学教育_国学经典名句 评论
- 2020-12-18 14:59钱文忠:我读《大学》《中庸》
- 2020-11-06 20:56命里一尺,难求一丈
- 2020-12-18 14:53读《大学》《中庸》《老子》《论语》的好处
- 2020-11-01 14:41你为什么命苦,因说话太强硬了,强硬态度决定命苦程度!
- 2020-12-18 14:56任蜜林:《大学》《中庸》不同论(大学言心,中庸言性)
- 2022-11-05 06:07《易经》:时刻保持警惕谨慎行事,反省修正自己的言行是成功的基石
- 2020-12-19 20:51《大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是谁写的?与《中庸》的作者是一个人吗?
- 2020-11-06 20:01100句顺口溜,串起中国文化常识(建议多读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