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清竹韵
刘孟浩博客-刘孟浩个人网站
当前位置:首页 » 国学大师_国学经典_国学教育_国学经典名句 » 正文
-
第一章 天心
吕祖曰:自然曰道,道名无相,一性而已,一原神而已。性命不可见,寄之天光,天光不可见,寄之两目。古来仙真,口口相传,传一得一。太上见化,东华传递某,以及南北两宗,全真可谓极盛,盛者盛其徒众,衰者衰于心传,以至今日,滥泛极矣,凌替极矣!极则返,故蒙净明许祖,垂慈普度,特立教外别传之旨,接引上根,闻者千劫难逢,受者一时法会,皆当仰体许祖苦心,必于人伦日用间,立定脚跟,方可修真悟性。我今叨为度师,先以太乙金华宗旨发明,然后细为开说。
太乙者,无上之谓。丹诀总假有为而臻无为,非一超直入之旨。所传宗旨,直提性功,不落第二法门,所以为妙。金华即光也,光是何色?取象于金华,亦秘一光字在内,是先天太乙之真炁,水乡铅只一位者此也。回光之功全用逆注,注想天心,天心居日月中。《黄庭经》云:’寸田尺宅可治生也‘,尺宅面也,面上寸田,非天心而何?方寸中具有郁罗肖台之胜,玉京丹阙之奇,乃至虚至灵之神所住。’儒曰虚中,释曰灵台,道曰祖土,曰黄庭,曰玄关,曰先天窍。盖天心犹如宅舍一般,光乃主人翁也。故一回光,周身之炁皆上朝,如圣王定都立极,执玉帛者万国;又如主人精明,奴婢自然奉命,各司其事。诸子只去回光,便是无上妙谛。光易动而难定,回之既久,此光凝结,即是自然法身,而凝神于九霄之上矣。心印经所谓’默朝飞升者是也‘。
宗旨行去,别无求进之法,只在纯想于此。《楞严经云》:‘纯想即飞,必生天上,天非苍苍之天,即生身于乾宫是也,久之,自然身外有身。’
金华即金丹,神明变化,各师于心,此种妙诀,虽不差毫末,然而甚活,全要聪明,又须沉静,非极聪明人行不得,非极沉静人守不得。”第二章:元神,识神
吕祖曰:天地视人如蜉蝣,大道视天地亦泡影。惟元神真性,则超元会而上之。其精气则随天地而败坏矣。然有元神在,即无极也。生天生地皆由此矣。学人但能守护元神,则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三界之中,此惟见性方可,所谓本来面目也。凡人投胎时,元神居方寸,而识神则居下心,下面血肉心,形如大桃,有肺以覆翼之,肝佐之,大小肠承之,假如一日不食,心上便大不自在,至闻惊而跳,闻怒而闷,见死亡则悲,见美色则眩,头上天心何尝微微些动也。问天心不能动乎?方寸中之真意,如何能动。到动时便不妙,然亦最妙,凡人死时方动,此为不妙,最妙者,光已凝结为法身,渐渐通灵欲动矣,此千古不传之秘也。
下识心,如强藩悍将,欺天君暗弱,便遥执纪纲,久之太阿倒置矣。今凝守元宫如英明之主在上,二目回光,如左右大臣尽心辅弼,内政既肃,自然一切奸雄,无不倒戈乞命矣。”
丹道,以精水、神火、意土三者为无上之诀,精水云何?乃先天真一之气,神火即光也,意土即中宫天心也。以神火为用,意土为体,精水为基。凡人以意生身,身不止七尺者为身也。盖身中有魄焉,魄附识而用,识依魄而生。魄阴也,知识之体也,识不断,则生生世世,魄之变形易质无已也。惟有魂,神之所藏也,魂,昼寓于目夜舍于肝,寓目而视,舍肝而梦,梦者神游也,九天九地,刹那历遍。觉则冥冥焉,渊渊焉,拘于形也,即拘于魄也。故回光所以炼魂,即所以保神,即所以制魄,即所以断识。古人出世法,炼尽阴滓,以返纯乾,不过消魄全魂耳。回光者,消阴制魄之诀也,虽无返乾之功,止有回光之诀,光即乾也,回之即返之也。只守此法,自然精水充足,神火发生,意土凝结,而圣胎可结矣。蜣螂转丸,而丸中生白,神注之纯功也。粪丸中尚可生胎离壳,而吾天心休息处,注神于此,安得不生身乎。
一灵真性,既落乾宫,便分魂魄。魂在天心,阳也,轻清之炁也,此自太虚得来,与元始同形。魄,阴也,沉浊之气也,附于有形之凡心。魂好生,魄望死。一切好色动气皆魄之所为,即识神也,死后享血食,活则大苦,阴返阴也,物以类聚也。学人炼尽阴魄,即为纯阳也。”第三章:回光守中
吕祖曰:回光之名何昉乎?昉之自文始真人也。回光则天地阴阳之气无不凝,所谓精思者此也,纯炁者此也,纯想者此也。初行此诀,乃有中似无,久之功成,身外有身,乃无中似有。百日专功,光才真,方为神火。百日后光中自然一点真阳,忽生黍珠,如夫妇交(百度)合有胎,便当静以待之,光之回,即火候也。
夫元化之中,有阳光为主宰,有形者为日,在人为目,走漏神识,莫此甚顺也。故金华之道,全用逆法。回光者,非回一身之精华,直回造化之真炁,非止一时之妄念,直空千劫之轮回。故一息当一年,人间时刻也,一息当百年,九途长夜也。凡人自哇的一声之后,逐境顺生,至老未尝逆视,阳气衰灭,便是九幽之界。故《楞严经》云:‘机在目’。《黄帝素问》云:‘人身精华,皆上注于空窍是也。’得此一节,长生者在兹,超升者亦在兹。此是贯彻三教工夫。
光不在身中,亦不在身外,山河大地,日月照临,无非此光,故不独在身中。聪明智慧,一切运转,亦无非此光,所以亦在身外。天地之光华,布满大千,一身之光华,亦自漫天盖地,所以一回光,天地山河一切皆回矣。人之精华,上注于目,此人身之大关键也。子辈思之,一日不静(百度)坐,此光流转,何所底止!若一刻能静(百度)坐,万劫千生,从此了彻。万法归于静,真不可思议,此妙谛也。然下手功夫,由浅入深,由粗入细,总以不间断为妙。功夫始终如一,但其间冷暖自知,要归于天空海阔,万法如如,方为得手。
圣圣相传,不离反照,孔云致知,释曰观心,老云内观,皆此法也。但返照二字,人人能言,不能得手,未识二字之义耳,反者,自知觉之心,反乎形神未兆之初,则吾六尺之躯,反求个天地未生之体,今人但一、二时中间静(百度)坐,反顾己私,便云反照,安的到头!
佛道二祖,教人看鼻尖者,非谓着念于鼻端也,亦非谓眼观鼻端,念又注中黄也。眼之所至,念亦至焉,何能一上而一下也,又何能忽上而忽下也。此皆误指而为月。毕竟如何?曰鼻端二字最妙,只是借鼻以为眼之准耳。初不在鼻上,盖以大开眼,则远视,而不见鼻矣。大开失之外走,易于散乱。太闭失之内驰,易于昏沉。惟垂帘得中,恰好望见鼻端,故取以为准,只是垂帘恰好,任彼光自然透入,不劳你注射与不注射。
看鼻端,于最初入静处举眼一视,定个准则变放下。如泥水匠人用线一般,彼自起手一挂,便依了做上去,不只管把线看也。
止观是佛法,原不秘的,以两眼谛观鼻端正身安坐,系心缘中,不必言头中,但于两〇中间起平处,系念便了。光是活泼泼的东西,系念两〇中间,光自然透入,不必着意于中宫也,此数语已括尽要旨。其余入静出静前后,以下止观书印证可也。
缘中二字极妙。中无不在,遍大千皆在里许,聊指造化之机,缘此入门耳。缘者缘此为端倪,非有定著也,此二字之意,活甚,妙甚。
止观二字,原离不得,即定慧也.以后凡念起时,不要仍旧兀坐,当究此念在何处,从何起,从何灭,反复推究,了不可得。即见此念起初也不要又讨过起处,觅心了不可得,吾与汝安心境,此是正观,反此者,名为邪观。如是不可得已,即仍旧绵绵去止,而继之以观,观而继之以止,是定慧双修,此为回光。回者,止也,光者,观也。止而不观,名为有回而无光,观而不止,名为有光而无回,志之。”第四章:回光调息
吕祖曰:宗旨只要纯心行去,不求验而验自至。大约初机病痛,昏沉散乱,二种尽之。却此有机窍,无过寄心息,息者自心也,自心为息,心一动,而即有气,气本心之化也。吾人念至速,霎倾一妄念,即一呼吸应之,故内呼吸与外呼吸,如声响之相随,一日有几万息,即有几万妄念。神明漏尽,如木槁灰死矣。然则欲无念乎?不能无念也,欲无息乎?不能无息也。莫若即其病而为药,则心息相倚是也。
故回光兼之以调息,此法全用耳光,一是目光,一是耳光。目光者,外日月交光也,耳光者,内日月交精也。然精即光凝定处,同出而异名也.故聪明总一灵光而已.坐时用目垂帘后,定个准则便放下。然竟放下,又恐不能,即存心于听息。息之出入,不可使耳闻,听惟听其无声也。一有声,便初浮不能入细,即耐心轻轻微微些,愈放愈微,愈微愈静,久之,忽然微者遽断,此则真息现前,而心体可识矣。盖心细则息细,心一动则炁动。定心必先之以养炁者,亦以心无处入手,故缘气为之端倪,所谓纯炁之守也。
子辈不明动子,动者以线索牵动言,即制字之别名也。即可以奔趋使之动,独不可以纯静使之宁乎。此大圣人,视心炁之交,而善立方便,以惠后人也。丹书云: ‘鸡能抱卵心常听’,此要诀也。盖鸡之所以能生卵者,以暖气也。暖气止能温其壳,不能入其中,则以心引炁入,其听也,一心注焉,心入则气入,的暖气而生矣。故母鸡随有时外出,而常作侧耳势,其神之所注未常少间也。神之所注,未常少间,即暖气亦昼夜无间,而神活矣。神活者,由其心之先死也。人能死心,元神活矣。死心非枯槁之谓,乃专一不二之谓也。佛云:‘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心易走,即以炁纯之,炁易粗,即以心细之,如此而焉有不定者乎。
大约昏沉散乱二病,只要静功,日日无间,自有大休息处。若不静(百度)坐时,虽有散乱,亦不自知。既知散乱,即是却散乱之机也。昏沉而不知,与昏沉而知,相去何啻千里!不知之昏沉,真昏沉也,知之昏沉,非全昏沉也,清明在是矣。
散乱者,神驰也,昏沉者神未清也,散乱易治,而昏沉难医。譬之病焉,有痛有痒者,药之可也,昏沉则麻木不仁之症也,散者可以收之,乱者可以整之,若昏沉,则蠢蠢焉,冥冥焉。散乱尚有方所,至昏沉全是魄用事也。散乱尚有魂在,至昏沉则纯阴为主矣。静(百度)坐时欲睡去,便是昏沉。却昏沉只在调息,息即口鼻出入之息, 虽非真息,而真息之出入,亦寄于此。凡坐需要静心纯炁,心何以静,用在息上,息之出入,惟心自知,不可使耳闻,不闻则细,细则清,闻则气粗,粗则浊,浊则昏沉而欲睡,自然之理也。虽然心用在息上,又善要会用,亦是不用之用,只要微微照听可耳。此句有微义,何谓照?即眼光自照。目惟内视而不外视,不外视而惺然者,即内视也,非实有内视。何谓听,即耳光自听,耳惟内听而不外听,不外听而惺然者,即内听也,非实有内听。听者听其无声,视者视其无形。目不外视,耳不外听,则闭而欲内驰。惟内视内听,则既不外走,又不内驰,而中不昏沉矣,此即日月交精交光也。
昏沉欲睡,即起散步神清再坐。清晨有暇,坐一柱香为妙。过午人事多扰,易落昏沉,然亦不必限定一柱香,只要诸缘放下,静(百度)坐片时,久久便有入头,不落昏沉睡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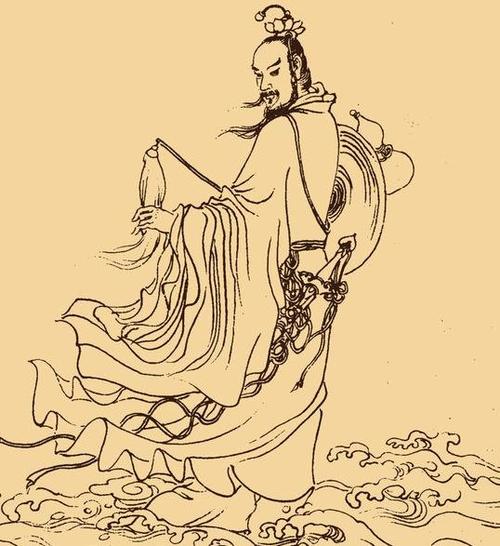
第五章:回光差谬
吕祖曰:诸子工夫,渐渐纯熟,然枯木岩前错落多,正要细细开示。此中消息,身到方知,吾今则可以言矣。吾与禅(百度)宗不同,有一步一步验证,请先言其差别处,然后再言验证,宗旨将行之际,予作方便,勿多用心,放教活泼泼地,令气和心适,然后入(百度)静,静时正要得机得窍,不可坐在无事中,所谓无记空也.万缘放下之中, 惺惺自若也,又不可以意兴承担,凡大认真,即易有此.非言不宜认真,但真消息,在若存若亡之间,以有意无意得之可也.惺惺不昧之中,放下自若也。又不可坠于蕴界,所谓蕴界者,乃五阴魔用事。如一般入定,而槁木死灰之意多,大地阳春之意少。此则落于阴(百度)界,其炁冷,其息沉,且有许多寒衰景象,久之便堕木石。又不可随于万缘,如一入(百度)静,而无端众绪忽至,欲却之不能,随之反觉顺适,此名主为奴(百度)役,久之落于色(百度)欲界。上者生天,下者生狸(百度)奴中,若狐仙是也。彼在名山中,亦自受用,风月花果,琪树瑶草,三五百年受用去,多至数千岁,然报尽还生诸趣中。此数者,皆差路也。差路即知,然后可求验证。”
第六章 回光验证
吕祖曰:验证亦多,不可以小根小器承担,必思度尽众生。不可以轻慢心承担,必须请事斯语。静中绵绵无间,神情豫悦,如醉如浴,此为遍体阳和,金华乍吐也。既而万籁俱寂,皓月中天,觉大地俱是光明境界,此为心地开明,金华正放也。既而遍体充实,不畏风霜,人当之兴味索然者,我遇之精神更旺,黄金起屋,白玉为台;世间腐朽之物,我以真炁呵之立生;红血为乳,七尺肉团,无非金宝,此则金华大凝也。第一段,是应《观今》云:‘日落大水,行树法象。’日落者,从混沌立基无极出.上善若水,清而无瑕,此即太极主宰,出震之帝也。震主木,故以行树象焉,七重行树,七窃光明也。西北乾方,移一为坎,日落大水,乾坎之象。坎为子方,冬至雷在地中,隐隐隆隆,至震而阳方出地上矣,行树之象也,余可类推矣。第二段,即肇基于此,大地为冰,琉璃宝地,光明渐渐凝矣。所以有篷台而继之有佛也,金性即现,非佛而何,佛者大觉金仙也。此大段验证耳。
现在验证,可考有三:
一则坐去,神入谷中,闻人说话,如隔里许,一一明了,而声入皆如谷中答响,未尝不闻,未尝一闻,此为神在谷中,随时可以验证;
一则静中,目光腾腾,满前皆白,如在云中,开阳觅身,无从觅视,此为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也;
一则静中,肉身絪緼,如绵如玉,坐中若留不住,而腾腾上浮,此为神归顶天,久之上升而可立待。
此三者,皆现在可验也。然亦是说不尽的,随人根器,各现殊胜。如《止观》中所云:‘善根发相是也。’此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须自己信得过方真。
先天一炁,即在现前验证中自讨,一炁若得,丹亦立成,此一粒真黍珠也。一粒复一粒从微而至著。有时时之先天,一粒是也,有统体之先天,一粒乃至无量是也。一粒有一粒力量,此要自己胆大,为第一义。”第七章:回光活法
吕祖曰:回光循循然行去,不要废弃正业。古人云:‘事来要应过,物来要识破。’子以正念治事,即光不为物转,光即自回。此时时无相之回光也,尚可行之而况有真正著相回光乎。
日用间,能刻刻随事返照,不者一毫人我相。便是随地回光,此第一妙用。清晨能遣尽诸缘,静(百度)坐一二时最妙。凡应事接物,只用返照法,便一刻无间断。如此行之,三月两月,天上诸真,必来印证矣”第八章:逍遥诀
吕祖曰:
玉清留下逍遥诀,四字凝神入旡穴。
六月俄看白雪飞,三更又见日轮赫。
水中吹起藉巽风,天上游归食坤德。
更有一句玄中玄,无何有乡是真宅。
律诗一首,玄奥已尽。大道之要,不外无为而为四字。惟无为,故不滞方所形象,惟无为而为,故不堕顽空死虚。作用不外一中,而枢机全在二目。二目者,斗柄也,斡旋造化,转运阴阳,其大药则始终一水中金,即水乡铅而已。前言回光,乃指点初机,从外以制内,即辅以得主。此为中、下之士,修下二关,以透上一关者也。今头绪渐明,机括渐熟,天不爱道,直泄无上宗旨,诸子秘之秘之,勉之勉之!
夫回光其总名耳。工夫进一层,则光华盛一番,回法更妙一番。前者由外制内,今则居中御外。前者即辅相主,今则奉主宣猷,面目一大颠倒矣。法子欲入静,先调摄身心,自在安和,放下万缘,一丝不挂。天心正位乎中,然后两目垂帘,如奉圣旨,以召大臣,孰敢不遵。次以二目内照坎宫,光华所到,真阳即出以应之。离外阳而内阴,乾体也。一阴入内而为主,随物生心,顺出流转,今回光内照,不随物生,阴气即住,而光华注照,则纯阳也。同类必亲,故坎阳上腾,非坎阳也,仍是乾阳应乾阳也耳。二物一遇,便扭结不散,絪緼活动,倏来倏去,倏浮倏沉,自己元宫中,恍若太虚无量,遍身轻妙欲腾,所谓云满千山也。次则往来无踪,浮沉无辨,脉住炁停,此则真交媾矣,所谓月涵万水也。俟其冥冥中,忽然天心一动,此则一阳来复,活子时也。然此中消息要细说,凡人一视一听,耳目逐物而动,物去则已,此之动静,全是民庶,而天君反随之役,是尝与鬼居矣。今则一动一静,皆与人居,天君乃真人也。彼动乃与之俱动,动则天根;静则与之俱静,静则月窟;静动无端,亦与之为静动无端;休息上下,亦与之为休息上下,所谓天根月窟闲来往也。天心镇静,动违其时,则失之嫩;天心已动,而后动以应之,则失之老;天心一动,即以真意上升乾宫,而神光视顶,为导引焉,此动而应时者也。天心既升乾顶,悠扬自得,忽而欲寂,即以真意引入黄庭,而目光视中黄神室焉,既而欲寂者一念不生矣。视内者,忽忘其视矣,尔时身心,便当一场大放,万缘泯迹,即我之神室炉鼎,亦不知在何处,欲觅己身,了不可的,此为天入地中,众妙归根之时也,即此便是凝神入炁穴。
夫一回光也,始而散者欲敛,六用不行,此为涵养本源,添油接命也。既而敛者,自然优游,不费纤毫之力,此为安神祖窍,翕聚先天也。既而影响俱灭,寂然大定,此为蛰藏炁穴,众妙归根也。一节中具有三节,一节中具有九节,俱是后日发挥。今以一节中具三节言之,当其涵养而初静也。翕聚亦为涵养,蛰藏亦为涵养,至后而涵养皆蛰藏矣。中一层可类推,不易处而处分矣,此为无形之窍,干处万处一处也。不易时而时分焉,此为无候之时。元会运世一刻也。
凡心非静极,则不能动,动动忘动,非本体之动也。故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若不感于物而动,即天之动也。是知以物而动,性之欲也,若不以物而自动,即天之动也。不以天之动对天之性,句落下说个欲字,欲在有物也,此为出位之思,动而有动矣。一念不起,则正念乃生,此为真意。寂然大定中,而天机忽动,非无意之动乎,无为而为,即此意也。诗首二句,全括金华作用。次二句是日月互体意,六月即离火也,白雪飞即离中真阴将返乎坤也。三更即坎水也,日轮即坎中一一阳将赫然而返乎乾也。取坎填离,即在其中。次二句说斗柄作用,升降全机,水中非坎乎。目为巽风,目光照入坎宫,摄召太阳之精是也。天上即乾宫,游归食坤德,即神入照中,天入地中,养火也。末二句是指出诀中之诀,诀中之诀,始终离不得,所谓洗心涤虑,为沐浴也。圣学以知止始,以止至善终,始乎无极,归乎无极。佛以无住而生心,为一大藏教旨。吾道以“致虚”二字,完性命全功。总之三教不过一句,为出死入生之神丹。“神丹”为何 ? 曰一切处无心而已。吾道最秘者沐浴,如此一部全功,不过“心空”二字,足以了之,今一言指破,省却数十年参访矣。
子辈不明一节中具三节,我以佛家“空、假、中”三观为喻,三观先空,看一切物皆空 ; 次假,虽知其空,然不毁万物,仍于空中建立一切事 ; 既不毁万物,而又不著万物,此为中观。当其修空观时,亦知万物不可毁,而又不著,此兼三观也。然毕竟以看得空为得力,故修空观。则空固空,假亦空,中亦空。修假观,是用上得力居多,则假固假,空亦假,中亦假。中道时亦作空想,然不名为空而名为中矣。亦作假观,然不名为假而名为中矣,至于中则不必言矣。吾虽有时单言离,有时兼说坎,究竟不曾移动一一句。开口提云:枢机全在二目。所谓枢机者用也,用即斡旋造化,非言造化止此也。六根七窍,悉是光明藏,岂取二目,而他概不问乎,用坎阳,仍用离光照摄,即此便明。朱子云阳师讳元育,尝云:“瞎子不好修道,聋子不妨。”与吾言暗合,特表其主辅轻重耳。
日月原是一物,其曰中之暗处,是真月之精,月窟不在月而在日,所谓月之窟也,不然自言月足矣。月中之白处,是真日之光,日光反在月中,所谓天之根也,不然自言天足矣。一日一月,分开止是半个,合来方成一个全体。如一夫一妇,独居不成室家,有夫有妇,方算得一家完全。然而物难喻道,夫妇分开,不失为两人,日月分开,不成全体矣。知此则耳目犹是也。吾谓瞎子已无耳,聋子已无目,如此看来,说甚一物,说甚两目,说甚六恨,六根一根也。说甚七窍,七窍一窍也。吾言只透露其相通处,所以不见有两,子辈专执其隔处,所以随处换却眼睛。第九章:百曰筑基
《心印经》云:“回风混合,百曰功灵。”总之立基百日,方有真光如。子辈尚是目光,非神火也,非性光也,非慧智炬烛也。回之百日,则精气自足,真阳自生,水中自有真火,以此持行,自然交媾,自然结胎,吾方在不识不知之天,而婴儿自成矣。若略作意见,便是外道。百日立基,非百日也。一日立基,非一日也。一息立基,非呼吸之谓也。息者自心也,自心为息,元神也,元气也,元精也。升降离合,悉从心起,有无虚实,咸在念中。一息一生持,何止百日,然百日亦一息也。
百曰只在得力,昼间得力,夜中受用,夜中得力,昼间受用。百日立基,玉旨耳。上真言语,无不与人身应。真师言语,无不与学人应。此是玄中玄,不可解者也。见性乃知,所以学人,必求真师授记,任性发出,一一皆验。第十章:性光识光
回光之法,原通行住坐卧,只要自得机窍。吾前开示云;“虚室生自”,光非白邪。但有一说,初未见光时,此为效验,若见为光,而有意著之,即落意识,非性光也。子不管他有光无光,只要无念生念。何为无念?干休干处得;何为生念?一念一生持,此念乃正念,与平曰念不同。今心为念,念者现在心也。此心即光即药。凡人视物,任眼一照去,不及分别,此为,性光,,如镜之无心而照也,如水之无心而鉴也。少刻即为“识光”,以其分别也。镜有影已无镜矣,水有象已无水矣。光有识尚何光哉!
子辈初则“性光”,转念则识,识起而光杳无可觅,非无光也,光已为识矣。黄帝曰:“声动不生声而生响”,即此义也。《楞严推勘入门》曰:“不在尘,不在识,惟选根”,此则何意?尘是外物,所谓器界也。与吾了不相涉,逐之则认物为己。物必有还,通还户牖,明还日月,借他为自,终非吾有。至于不汝还者,非汝而谁。明还日月,见日月之明无还也。天有无日月之时,人无有无见日月之性。若然则分别日月者,还可与为吾有耶。不知因明暗而分别者,当明暗两忘之时,分别何在,故亦有还,此为内尘也。惟见性无还,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则见性亦还矣。还者还其识念流转之见性,即阿难使汝流转,心目为咎也。初入还辨见时,上七者,皆明其一一有还,故留见性,以为阿难拄杖。究竟见性既带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传送识、阿赖耶识),非真不还也。最后并此亦破,则方为真见性,真不还矣。子辈回光,正回其最初不还之光,故一毫识念用不着。使汝流转者,惟此六根,使汝成菩提者,亦惟此六根。而尘与识皆不用,非用根也,用其根中之性耳。今不堕识回光,则用根中之元性,落识而回光,则用根中之识性,毫厘之辨在此也。用心即为识光,放下乃为性光。毫厘干里,不可不辨。识不断,则神不生;心不空,则丹不结。心净则丹,心空即药。不著一物,是名心净,不留一物,是名心空。空见为空,空犹末空,空忘其空,斯名真空。第十一章坎离交媾
凡漏泄精神,动而交物者,皆离也。凡收转神识,静而中涵者,皆坎也。七窍之外走者为离,七窍之内返者为坎。一阴主于逐色随声,一阳主于返闻收见。坎离即阴阳,阴阳即性命,性命即身心,身心即神照。一自敛息精神,不为境缘流转,那是真交。而沉默趺坐时,又无论矣。第十二章:周天
周天非以气作主,以心到为妙诀。若毕竟如何周天,是助长也,无心而守,无意而行。仰观乎天,三百六十五度,刻刻变迁,而斗柄终古不动,吾心亦犹是也。心即璇玑,气即众星。吾身之气,四肢百体,原是贯通,不要十分着力。于此锻炼识神,断除妄见,然后药生,药非有形之物,此性光也。而即先天之真气,然必于大定后方见,并无采法,言采者大谬矣。见之既久,心地光明,自然心空漏尽,解脱尘海。若今日龙虎,明日水火,终成妄想。吾昔受火龙真人口诀如是,不知丹书所说更何如也。
一日有一周天,一刻有一周天,坎离交处,便是一周。我之交,即天之回转也。未能当下休歇,所以有交之时,即有不交之时。然天之回旋也,未尝少息。果能阴阳交泰,大地阳和,我之中宫正位,万物一时畅遂,即丹经沐浴法也。非大周天而何 ? 此中火候,实实有大小不同,究竟无大小可别。到得工夫自然,不知坎离为何物,天地为何等,孰为交,孰为一周两周,何处觅大小之别耶。总之一身旋运,虽见得极大亦小,若一回旋,天地万物,悉与之回旋,即在方寸处,亦为极大。金丹火候,要归自然。不自然,天地自还天地,万物各归万物。欲强之使合,终不能合。即如天时亢旱,阴阳不和。乾坤未尝一日不周,然终见得有多少不自然处。我能转运阴阳,调适自然,一时云蒸雨降,草木酣适,山河流畅,纵有乖戾,亦觉顿释,此即大周天也。
问活子时其妙,必认定正子时似着相,不着相不指明正子时。从何识活子时,即识得活子时,确然又有一正子时,是二是一,非正非活,总要人看得真,一真则无不正,无不活矣。见得不真,何者为正,何者为活耶。即如活子时,是人所时时见得的。毕竟到正子时,志气清明,活子时愈觉发现。人未识得活的明了,只向正的时候验取,则正者现前,活者无不神妙矣。第十三章:劝世歌
吾因度世丹中热,不惜婆心并饶舌。世尊亦为大因缘,直指生死真可惜。
老君也患有吾身,传示谷神人不识。吾今略说寻真路:黄中通理载大易,
正位居体是玄关。子午中间堪定息,光回祖窍万神安。药产川原一气出,
透幕变化有金光。一轮红曰常赫赫,世人错认坎离精。搬运心肾成间隔,
如何人道合天心。天若符合道自合,放下万缘毫不起。此是先天真无极,
太虚穆穆朕兆捐。性命关头忘意识,意识忘后见本真。水清珠现玄难测,
无始烦障一旦空。玉京降下九龙册,步云汉今登天关,掌雷霆兮驱霹雳。
凝神定息是初机,退藏密地为常寂。
吾昔度张珍奴二词,皆有大道。子后午前非时也,坎离耳。定息者,息息归根,中黄也。坐者,心不动也。夹脊者,非背上轮子,乃直透玉京大路也。双关者,此处有难言者。地雷震动山头雨者,真气生也。黄芽出土者,药生也。小小二段,已尽修行大路,明此可不惑人言。
昔夫子与颜子登泰山顶,望吴门白马,颜子见为疋练,夫子急掩其目,恐其太用眼力,神光走落,回光可不勉哉!
回光在纯心行去,只将真息凝照于中宫,久之自然通灵达变也。总是心静照定为基,心忘气凝为效,气息心空为丹成,心气浑一为温养,明心见性为了道。子辈各宜勉力行去,错过光阴可惜也。一日不行,一日即鬼也。一息行此,一息真仙也。勉之!勉之金花的秘密--太乙金华宗旨白话文
天心第一
吕祖说:自然,就是道。道没有名义,没有形像;仅仅是一个性和一个元神而已。性命是看不见,也摸不着,只寄托在天光上,天光也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寄托在两眼上。
自古以来仙真传道,都是口口相传,传授一代,成功一代,自从太上点化东华,一直递传到我吕某,以及南北两宗的徒众,全真道教可称谓极盛了;不过说是盛,盛在人数众多;其实是衰,衰在心传断绝,直致今日,真是泛滥到极点,凌替到了极点,物极必反。于是净明派的许祖站出来慈悲普渡,提出教外别传的原则,来接纳根器不凡的人,听道者可算是千载难逢,学道者可算一时机遇,大家都要体会许祖度人的苦心,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和待人处世方面立定脚跟,然后才能谈到修真悟性。我现在荣幸的担任度师,先讲解一下「太乙金华宗旨」,以后再逐章细为介绍。
所谓「太乙」者就是无上的代名词之称,一般炼功的法诀虽有很多种法,但都要借有为之术,以达无为之境,所以并不是一步登天的功法。而这里所传授的宗旨有些不同,一开头就直接提出性功,不落第二法门,所以更为玄妙。
所谓「金华」也就是光。那光有什么颜色?不过取像于金质的华采。用这个名词,内涵包藏着一个「光」字在内,这就是先天太乙的真气。入药镜所说:「水乡铅,只一味」者,就是说这个。
回光的功夫,全用逆法,注想天心。天心是位居于日和月(左右眼)的中间。黄庭经云:「寸田尺宅可治生。」的话,那尺宅,指的是人的面部;面部有块一寸见方的田,那不是指天心,又是指什么?这一方寸的地方,居然有森罗萧台之胜景,玉京丹阙之奇观,它是最虚最灵的神居住之处,儒家称它为「虚中」;释家称它为「灵台」;道家的称乎更多有「祖土」、「黄庭」、「玄关」、「先天窍」等等。原来那天心就像一家宅院一样;那光是这家宅院的主人翁,所以只要一回光,则周身之气都要上朝头顶,就像圣王定都建朝,万邦都持有玉帛前来朝贺;又像主人精明,奴婢自然俯首听命,各司其职。
各位只要实行回光,就是无上妙谛。不过要注意,那光易动而难定,回光一久,那光就会渐渐凝结成自然法身,最终能够凝神于九霄之上。心印经所讲的「默朝上帝,一纪飞升」者就是指此也。
实行宗旨,别无更进一步的功法,只在纯想天心。楞严经云:「纯想即飞,必生天上」。那天,并不是指蓝蓝的天,而是隐喻法身在干宫(头顶)生成是也。干为天,日久天长,自然就会身外有身。
金华也就是金丹,它的神明变化,随各人的心而不同。这里面的妙诀,虽然没有丝毫差池,然而这功法却十分灵活。全靠聪明,又要沉静。故不是最聪明的人不能实行,不是最沉静的人不能坚持。
元神识神第二
吕祖说:天地看人,好象朝生暮死的蜉蝣;而大道看天地,也像水中的泡影;它们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惟有人类的元神真性,能够超越悠久的元会年代,更长期的存在着。但人们的精和气,却随着天地而腐朽败坏,仍然不能持久。好在还有元神存在,它就是所谓「无极」;天地都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因此,学道的人只要把元神守护住,就可以超生在阴阳之外,不在三界之中。不过,这必须要见到真性才行,而真性就是所谓本来面目。
人类从投胎时期起,那元神就安住在那一寸见方的地方,而识神却安住在下面的心脏里,下面那颗血肉之心,形状像一只大桃子,有肺协覆盖着它,肝协依傍着它,大小肠承接着它。假如人们一日不吃食物,心上就觉得老大不自在。那颗心听到可惊的信息,就蹦蹦的跳;听到愤怒的信息,就沉沉的闷;见死亡的情景,就感到切切伤悲;见到绝色的美女,就飘飘然昏眩起来。可是头上何尝有一丁半点的闪动?
如果要问:天心难道不能动吗?
答复是:方寸处的真意,怎样能动呢?如果它真动了,事情就不妙了,但却也是最妙。一般人死的时后天心才动,所以叫做不妙;而最妙,是指那神光已凝结成了法身,渐渐灵通,它就跃跃欲动。这些话可是千古不传之秘语啊。
人类的下识心,就像专横跋扈的诸侯和军阀,欺负上面君主孤立,在外边遥执朝纲;久而久之,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发生篡权夺位的事。现在如果凝聚神光照定元宫(天心),好比英明的君主,有了伊尹周公那样的贤臣辅佐;两眼回光,好比左右大臣尽心参正,结果政治清明,这时,自然一切奸臣乱贼,无不倒戈乞命了。
养生大道是把精(属水)、神(属火)、意(属土)这三件,当作无上之宝。精水是什么?乃是先天真一之气。神火就是光。意土就是中宫天心。以神火为用,意土为体,精水为基。
人身是由「意」产生出来的,这里所说的「身」不仅是七尺血肉之躯,因为身中还有魂和魄,魄附在「识」上而产生作用;识依在魄上得以生存。魄是阴性的,是识的具体。如果识不断绝,那么随便你生死轮回多少次,魄一直存在着,只是跟着变个形,般个家而已。惟有魂是藏神的场所,魂在白天安住在眼睛里,夜晚睡眠,就安住在肝里,在眼里时,使人能看;在肝里时,使人做梦,梦就是神在游荡。那怕九天九地,一剎那间也可以走遍,但醒来之后却昏昏然什么也不记得了。那是受到形体的拘束,也就是受到魄的制约。所以回光就是为了炼魂,为了保神,为了制魄,为了断识。古人修道,主张炼尽阴性的渣滓,返回纯阳的境界,其实不过是消魄保魂而已。
我们提出的回光功法,正是消阴制魄的诀窍;里面虽无返还干阳之功,却有札札实实的回光口诀。所谓光就是干阳;所谓回就是返还。只要坚持这一功法精水自然充足,神火自然发生,意土自然凝定,最后可以结成圣胎。请看蜣螂不断搓滚那泥团丸,而泥丸里居然产生一种白色物质,这可说是一种神注的纯功。连粪团丸里都可以产卵、结胎、孵化、出壳;那么我们天心这一块元神休息的宝地,如果能集中意念,哪能不产生出法身来呢?
人们那种灵妙的真性,在头部干宫落脚之后,便分出了魂和魄。魂住在天心,属阳性,是一种轻清之气,来自浩瀚的太空,与「元始」是同一类型。而魄属阴性,是一种沉浊之气,附着在有形的凡心上。魂让人求生,魄却让人找死。一切好色、动气的坏习性,都是魄所操纵的,那也就是「识神」。魄在人死之后能享受血食,但人活着的时候它却很苦。其所以死后更乐,是因为从阴性返回到阴界,正是物以类聚。学道的人如果能炼尽这种阴魄,当然就成为纯阳之体了。
回光守中第三
吕祖说:回光这个名词,始于何人?始于文始真人(关尹子)。回光的时候,则天地间阴阳之气无不凝聚,所谓「精思」,所谓「纯气」讲的都是这回事。开始实行这一个功诀时,是「有中似无」;日久功成,达到身外有身的地步,那就是「无中生有」。要专心炼功一百天,那光才达到真的地步,那才是真正的神火。在一百日之后,光自然会凝聚;人身中的一点真阳,忽然产生黍粒大小的光珠,就像夫妇交合会怀胎一样,此时必须平静地去等待。光的回法,以及回的程度,就是人们常说的「火侯」。
在广袤的造化之中,有阳性的光在作为主宰。有形体的就是太阳;在人身中就是两眼,通过眼光走漏神识出去,那就是最顺当。所以金华功法,就不能让它顺当,而是采用一种逆法。
要知道回光不仅是返回一身的精华,而且是返回造化中的真气;不仅是制止一时之妄想,也是解脱了千劫之轮回。所以说把一呼一吸的时间当作一年,就是人间的时刻;把一呼一吸的时间当作百年,那就是九泉之下的漫漫长夜。
人自从娘胎中叻地一声诞生出世,从此就顺着环境生活,一直到老,从来不曾逆视过。阳性的气逐渐衰微,逐步走进那阴性的九幽之界。所以楞严经云:「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你们学道的人原是「想」少「情」多,因而沉沦在下道之中,只有内观于息静,才能成为正觉,这里用的正是那种逆法。在锻炼中眼睛最为重要。阴符经云:「机在目。」黄帝素问也云:「人身精华,皆上注于空窍。」都在强调这个。你们懂得了这一章所讲的道理,长生之方就依靠它,飞升之术也是依靠它。这是贯通了儒、释、道三教的功夫原理。
光并不在身中,但也不在身外。请看山河大地,日月光华照耀着它们,所以光不独在身中。聪明才智,一切事物的正常运转,亦无一不依靠此光,所以它也并不在身外。天地的光华,布满了大千世界;一身的光华也可说是铺天盖地。因此只要你一回光,那山河大地,一切事物也跟着回光了。
人的精华是向上凝集在眼睛中的,这可是人身上一大关键。你们想一想,假如一天不静坐,那光随视觉而流转,能有个完吗?如果能抽出一会儿的时间来静坐,即使是万劫千生,在其中也能了彻。万法终归于静,这一条是真不可思议呵!这真是最玄妙的道理。然而着手炼功,还是由浅入深,由粗入细,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不间断的炼为妙。功夫始终是一贯的,不过在炼功过程中,却冷暖自知,只能由个人去体会了,总之要达到海阔天空,万法如如这种境界,才算是入门得手。
自古以来,圣师代代相传,从未离开「反照」这一说。孔子云:「致知」,释迦号:「观心」,老子云:「内观」,皆是指此一法也。但是「反照」这二个字,人人都会说,却大都不能做到入门得手;其主要原因是还不懂这二字的真正函义。「反」者,就是从有知有觉的心,返回到自己身体和精神还未形成的那种阶段去;也就是在自己六尺之躯当中,反求那个天地尚未形成以前的本体,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学道的人,只知道每天静坐一二小时,反思一下自己种种的行为,便说做到了「返照」,那怎能叫彻底呢?
佛道二教的教祖,叫人静坐时观看鼻尖,这并不是让你把意念集中在那鼻端那里;也不是让你把眼观盯着鼻端,而意念又集中在中黄部位。因为眼睛所到之处,心意也跟着到此处;心所到之处,气也跟着到了。这怎么能一上又一下?又怎么能忽上忽下?照这种理解法,正应了楞严经里所说的「认指为月」的妙谕了,什么是「认指为月」,就是说有人用手指指着月亮给人看,那人没看月亮,只看着他的手指。回归正传,那么究竟要怎么办才好?我说就是这「鼻端」二字最妙!这只不过是借鼻端来作眼睛的标准,本意并不是在鼻子上面,因为静坐时,眼睛开得太大,就看得过远,于是看不见鼻子了。眼睛闭得过头,就等于合上了眼,于是更看不见鼻子了。太开的缺点,是眼睛外走,容易产生散乱现象;太闭的缺点,是眼光内驰,容易产生昏沉现象。惟有眼垂帘得适中,恰好能望见鼻尖端,最为恰当,所以取鼻端以为标准。这只是让你垂帘的做到恰到好之处,使光自然透入,无需你主动注射或不注射。
眼睛看鼻端,只是在最初快要入静时,举目一视,定个准则,然后你就放下不去管他。好比泥水匠人砌墙挂线一般,他把线挂起来,便照着这线一直往上砌,并不需要一边在砌,一边老是注意去看线。
止观的功法原是佛家的法,并没有什么秘密。那功法内容是以两眼仔细观看鼻尖,然后正身安坐,把心联系在「缘中」部位。佛家言「缘中」,就是道家所说的「中黄」同一道理。也不必把那里称作头部之中。初学的人,只须于两眼中间与眼珠齐平之处,联系意念就可以。光是活泼泼的东西,在两眼齐平处联系意念,那光就会自然而然的透入,并不必要将意念集中在中黄部位。我这几句话,已经括尽佛家功法的要领,其余入静、出静前后应注意事项,大家可以参考隋代智顗大师所着的《小止观书》印证。
缘中这二个字下得妙极了!无所不在是为「中」;整个大千世界都可以包括在里面,聊以指示造化之机,必须缘着这条路入门。所以「缘」字,就是「缘」着这一起点来开端,来萌芽,不是叫你定定地去攀缘着它,此二字的意义,真是太活了,太妙了!
「止」和「观」这二个字,原是离不开的,那也就是「定」和「慧」也。以后大家在静坐时,如果有染念出现时,不要仍旧死死的坐在那里,可以找一找这个念头出现在何处?从何而起?又从何而灭?反复追究,一直追到追不出结果来,那就是念头生起之处。但你决不要去硬找那念头起处,最适合是达到所谓「觅心了不可得,吾与汝安心竟。」这种程度,像这样才是正观,若不是这样,就不是正观,叫做「邪观」。寻找念头而不可得,以后,还会有新的念头生出来,那么仍然绵绵地止住它,接着又去观它,观到合适的程度,就再去止住那观的念头,这种功法,是一种定慧双修法的功法,也就是我前面所讲的回光。回者就是止;光者就是观。止而不观,称为有回无光;观而不止,称为有光无回。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一点。
回光调息第四
吕祖说:「宗旨」只要专心实行去做,不求验而效验自来,大致说,初学静坐的人,不外乎有昏沉和散乱二种毛病。要治疗这种毛病的方法,无过于把心用在调息上面,「息」者这个字,由「自」「心」两字组成,所以说「自心为息」的确,心一动,就有了气息,气息本是心所化出。我们心中的念头来得很快,一霎那间就会产生一个妄念,相应的就有一次呼吸,念头是内呼吸,气息是外呼吸,就像声波和音响一样的相随相应,一天之中有几万次呼吸,就有几万个妄念,像这样下去,人的精神就会耗尽,最终成为槁木死灰。那么干脆就不产生念头了吧?那不行,没有念头是做不到的,这好比说干脆不要呼吸一样,那明明是做不到的事。不如就这个病,下这个药,将心和息紧紧依靠在一起。用这种方法来统一它们。所以在回光时,同时也要调息,调息功法全用耳光。回光是用眼睛,而调息则用耳光;眼光在外,相当于日月交光。耳光在内,想当于日月交精。那精就是光的凝定状态,实际上是同出而异名。人的聪和明,总而言之只是一灵光而已。
静坐时,先将两眼垂帘后,定个准则,然后将万虑放下。但就这样放下,恐怕也做不到。那么就存心于听呼吸的声音。使气息的出入,不能让耳朵听到。听是听其无声,一有了声,那就说明气息粗浮,还未入细;必须耐心的把呼吸再放轻微一些,静细一些,照这样愈放愈微,愈微愈静,久而久之,忽然连那微细的气息也突然断了。那时真息就来到你的面前,心的本来面目就能觉察到了。因为心一细,气息也会跟着细;只要意念专一,就可以调动真气,呼吸一细,心也会跟着细,只要气息专一,就可以调动心神。古人主张在定心之前,先要养气;也是对于心意无处着手;所以借调习作定心之开端,这就是所谓「纯气之守」。
各位还不明白调「动」的意义。动,拿线索牵动来做比喻,那就是「掣」字的别名。物体可以用线索拉着跑,使它动起来;心神难道就不可以用纯静来使它安定下来吗!这是大圣人观察到心和气的交互关系,总结出来的简便方法,用以惠赐后人。
养生书上说:「鸡能抱卵心常听,」这是一句妙诀。你看母鸡孵蛋,用的是暖气,但那暖气只能去暖蛋壳,而不能贯入蛋中;只有用心来把暖气引进去。母鸡抱
蛋时专心的听,一心专注,心进入蛋内,气也随着进入,蛋得到了暖气,于是发育出小鸡。母鸡孵蛋时期,有时也出外走走,不过牠经常作侧耳而听的姿势,心神还是专注在蛋上,一直没有间断,于是神就活了。神的活是由于心的先死。人如果先能死心,元神也就会活。但这里所讲的死心,不是使心枯槁而死,乃是使心专一不分。佛家常说:「置心一处,无事不办,」心容易走,就用气来安定它;气容易粗,就用心来微细它。照这样办,还会有心神不定的情况吗。
大体上昏沉和散乱二种毛病,只要静功功夫每天不间断,自然会有很大的改善。如果不去静坐,虽然一直存在着散乱,自己也不知道。现在知道有散乱这种毛病存在,那就是消除散乱的开端了。昏沉而不自觉,与昏沉而自己能发觉,两种相比,何只相去千里!不被发觉的昏沉,才是真正的昏沉;知道自己在昏沉,还不是完全昏沉,因为其中还有清楚明白在里边。
散乱是神在游动,昏沉是神不清楚。散乱易治,昏沉难医。好比生病一样,有痛的,有痒的,对症下药就可以把它治好;而昏沉好比是麻木不仁的症候,不大好治。散的可以收拢;乱的可以去整理;而昏沉则是蠢蠢然、冥冥然的,真不好下手。散乱还有个境界,而昏沉则全是魄在操纵。不像散乱时尚有魂在,而昏沉时,则纯是阴气为主。
静坐时昏昏欲睡,那就是昏沉的毛病来到了。消除昏沉的办法是在调息,息就是口呼鼻吸,出入之气,虽然不是真息,但真息的出入,却寄托在这一呼一吸上面。静坐时,先要静心纯气。心怎样静?用在息上,息的出入,惟有心理明白,不能让耳朵所听见。听不见,息就细,息一细,气就清。听得见,息就粗,息一粗,气就浊。气浊当然就会昏沉而想睡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过把心用在息上,又要善于运用,那是一种不用之用,不要过于认真,只要微微照听一下就行了。
怎样去照?是用眼光自照。两眼只向内视而不向外视;眼睛不外视,当然就是内视。并非真正有一种内视方法。怎样去听?就是用耳光自听,两耳只向内听而不向外听,听是听其无声,视是视其无形;仅仅是单纯的眼不向外视,耳不向外听,心神会因闭塞住了而想内驰;只有做到内视、内听,于是心神既不能外走,又不能内驰;处在中间,那就不会昏沉了。这就是日月交精和交光的方法。
实在昏沉欲睡,就不要勉强去坐,应当起来散步一下,等神清之后再坐。清晨起来有空,静坐一柱香的时间为最妙。过了中午,人事多扰,静坐中容易发生昏沉,但也不必限定必须要坐一柱香的时间;只要把各种染念包袱放下,高质量的静坐片刻,久而久之就会有所进步,再也不会产生昏沉欲睡的现象。
回光差谬第五
吕祖说:各位现在的功夫渐渐纯熟了。不够俗话说:「枯木岩前错路多」,我还要细细的给大家阐述一下,这里边的消息,真是身到方知,但现在我可以对大家详细讲了。
我道家功法与禅学不同,那是一步有一步的效验。请允许我先讲差异之处,然后再谈效验。在将要实行「宗旨」功法的时候,预先要作好准备,不要多用心,使心神活活泼泼地,让气息和平,心神恬适,然后再静坐。
入静时,正要得机得窍,不可坐在一种无所事事的硬壳里,在放下一切感觉和思虑当中,心神依然要和平常一样的清醒;但又不能兴致勃勃地放下万念那就太过分了。在清醒而不胡涂之中,自自如如的放下万念;然又不能放任自流,以致堕入蕴界。所谓「蕴界」是指色(形象)、受(感觉)、想(意象)、行(意志)、识(意识),五种阴魔的活动。
有些学道者在入定的时候,槁木死灰的气象多,大地阳春的气象少,这就是落在阴界里去了,他的气是冷的,他的息是沉的,里面还有许多寒衰景象,照这样修炼下去,日久就成了木头和石头了。
既要扭转这种死气沉沉。但又不能追随万缘。如果在静坐时,无缘无故地各种思绪纷纷来临,消除它们又消除不掉;听任它们来来往往,反而觉得顺当舒适;这种情况叫做「主为奴役」。照这样修炼下去,日久就落入色欲界里面去了。运气好的还是做人,运气不好的就下生做了哺乳动物,比如说成了狐仙。狐仙牠在名山之中,也还算是享福。那些风月花果,奇树异草,三五百年尽牠享用,寿命长的可以到几千年。但到头来,还是要进入生死轮回,回到烦恼的世界里来。
以上说的几种,都是差路也。知道了差路,然后就可以谈到效验了。
回光证验第六
吕祖说:回光的证验也多,这不能以小根、小器来对待,而要有渡尽众生的襟怀;更不可以用轻心、慢心来对待,而要按照我所讲的内容去实行。
入静中间感觉到绵绵而不间断,心情愉快,心神舒适,好象处在微醉之中,沐浴之后;这就是遍体阳和,金华初露的象征。随后又觉得万籁无声,一轮皓月升到中天,大地全都成为光明世界;这就是心体开明,金华正放的象征。随后又感觉到全身非常的充实,有不畏风霜的气概,别人感到兴未索然的事,我遇到了却精神更旺;就像用黄金建屋,用白玉筑台,世间上腐朽的东西,我用真气来呵它,它立刻就恢复生机;红血变成了乳汁。我这七尺血肉之躯,似乎全是金宝所构成的,有了这种象征,就达到了金华大凝的阶段。
第一段效验,正如佛家《观无量寿经》要求观想的「日落」「大水」「行树」等种种初期「法象」。日落景象,象征着混沌之中,由无极打下基础。大水景象,符合「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清洁无瑕,那就是由无极进化成的太极主宰,也就是易经说卦所谓的「帝出乎震」。震在八卦中属木,所以又用「行树」来作为表象。经中所说的「七重行树」,象征的七窍光明。
第二段效验,是从第一段奠基而来的。观想大地变成冰雪世界,化为琉璃宝地,光明逐渐凝聚;于是以后观想的景象中,就出现了篷台,而继之出现了诸佛。金性显露,那不就是佛吗?「佛」是译音,本就是「大觉金仙」。上面所讲的是整个功法修炼中大段的效验。
当前大家能够印证的效验,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入静之后,神进入谷中,听到外边有人说话,声音就像隔了一里多路似的,但又清楚而明了;那声音进入耳鼓,好象深山大谷中的回声,未尝听不见;但又未尝能听得见。这种神入谷中的现象,大家随时可以体验到。
一种是在入静之中,眼光腾腾散开,前面一片白色,就像在云彩当中,即使睁开眼去看自己的身体,也无从看见,这种现象称为「虚室生白」,那是内外通明,吉祥止止的征象。
一种是在入静之中,肉体温暖和软,又像棉花,又像碧玉,坐在那里好象留不住似的,有腾腾上浮的感觉。那是因为神归头顶之天;久而久之,身体的升空是可以实现的。
这三种,都是现在可验证的景象。然还有许多效验是说不尽的,随各人的素质不同,而产生各种不同妙景。正如《止观书》所列举的那种:「善根发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总之一句话,必须自己信得过,那才是真切。
先天一气,可以在当现前这些效验中去寻找。找到了先天一气,丹也就可以炼成。这可是一粒真正的黍珠。正如张伯端《金丹四百字》所说「一粒复一粒,从微而至着。」先天,也有阶段性的先天,就是上面所讲的「一粒」;也有整体性的先天,就是从一粒乃至无穷粒。不过一粒有一粒的力量。最重要的第一义,是必须自己决心大。
回光活法第七
吕祖说:回光功法按步就班的去实行,也不要影响自己的正业。古人云:「事来要应过,物来要识破」。你们在日常生活中用正念行事,那光就不会随物而转移。遇事以正确态度对待,光随时可以返回,这叫做时时刻刻作无形无相的回光。
日常生活中,能够时时处处做返照功夫,又不着人相,又不着我相,一丝一毫也不耿耿于怀,那就是等于随时随地在回光,这才是「宗旨」的第一妙用。
清晨起来,排除各种干扰,静坐一二个小时,那就是最妙。不过,就在平常的一切待人接物活动中,练习返照法,能够做到没有一刻间断;照此实行之两月、三月,也会感动天上仙真,来与你印证了。
逍遥诀第八
玉清留下逍遥诀,四字凝神入气穴;
六月俄看白雪飞,三更又见日轮赫;
水中吹起藉巽风,天上游归食坤德;
更有一句玄中玄,无何有乡是真宅。
我这一首律诗,已经把功法的玄奥说尽了。大道的要领,不外乎「无为而为」四个字。惟有无为,才不凝滞在范畴和形象之上;惟有以无为而行有为,才不致堕入顽空死虚之中。其中的作用不外乎一个「中」字;而枢机全在两眼。两眼就好比那北斗星的斗柄一样。造化的斡旋,阴阳的转运,全都靠着它。而大药,始终只是一「水中金」这一味。
前面所讲的回光功法,是用来指点初学的人,从外部来控制内部,用臣佐来保证君王。这里是为中下之士修下两关,来透入上面那一关提出的功法。现在修行道路逐渐明朗,功法关键已逐步纯熟。上天不爱惜那珍贵的道法,让我直接透露出那至高无上的宗旨。你们各位要珍惜啊!勉力啊!
回光,是功法的总名称。但功夫上进一层,则光华也盛大一番,回光方式也更妙一些。前面功法是由外部而控制内部,现在功法则是由中央而驾驶外围;前面功法是用臣佐来保证君王,而现在功法则是奉君王圣旨来发号施令,面目完全是一大颠倒。
这一功法的内容是在欲入静之前,首先要调身调心,使它自在安和,接着放下万缘,丝毫没有牵挂。让天心正位于中央,然后两眼垂帘,就象奉了圣旨去召唤大臣,谁敢不尊?接着就用两眼的目光内照坎宫(丹田),光华所到之处,真阳就会出来应接。
八卦中的离(),外部是阳而内部是阴。它的本体原是干卦(),一个阴爻进入内部,却成为主人。于是随物而生心,顺出而流转。现在回光内照,不随物而生心,那阴气就受到了控制;同时由于光华的注射,逐步变成了纯阳。又因同类相亲,会调动那坎卦()中间的阳爻向上升腾。这一阳爻原非坎阳,实际上也是干阳,所以,仍然属于干阳应接干阳。这二件物体相遇,就是纽结不散,氤氲活动,忽来忽往,忽浮忽沉。这时自己元宫之中(指胸腹腔),犹如太空那样无边无际,全身轻妙无比,飘飘然好象要上升,这就是所谓「云满千山」。接着,那气机来往无踪,浮沉无迹,忽然脉也停住了,气息也停了。这种状态在养生书中称为「坎离交媾」;这就是所谓「月涵万水」。等到在那杳杳冥冥之中,忽然天心一动,这就是一阳来复,活子时出现了。但这里面的消息还要细说。
一般人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那眼和耳一直是随外物而动的,外物走了,看和听的行为也结束了。这里头的动静,就好比是下边臣民办事,而上面的天子反而随着他们去服务一样。这样下去,无异是跟鬼住在一起了。现在我们炼功的人,一动一静,不是跟鬼在一起,而是跟人在一起。那人,就是真人,就是自己身中的天子。天子一动,下面的臣民一齐跟着动;这种动就称为「天根」。天子一静,下面臣民也一齐跟着静;这种静就称为「月窟」。天子动静无端,臣民们也随着动静无端;天子休息上下,臣民们也跟着休息上下;这就是所谓「天根月窟闲来往」。
天心处在镇静之中,气机动得过早,火侯就失之太嫩;天心已经在动,那气机在后面才动,火侯就失之太老。正确的方式,是天心一动,立刻用真意导引气机向干宫(头顶)上升,两眼的神光也注视顶部作为引导,这就是动得恰到时机。天子已经上升到干宫,正在游扬自得时,忽然那运动似乎要停止下来;这时应当赶快用真意引导他下降到黄庭部位(中丹田),而眼光内视那「心后关前」的中黄神室。接着,气机运动又要停止,那是一念不生的结果。这时眼光向内注视的意念,也忽然淡忘了,身心来了一场大解放,万感千念一时泯灭;自己神室中炼丹的炉鼎(鼎指着中丹田,炉指着下丹田),也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甚至连自己的身体在什么地方,也找它不到。如果进入这种境界,就叫作「天入地中」,那就是众妙归根的时刻。到了这一阶段,才是所谓「凝神入气穴。」
按照回光功法次序来印证,在实行回光的时候,开始那光像一盘散沙,后来逐渐有了收敛的趋势,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功能,好象都要停止运行了,这就是「涵养本源,添油接命」一节功法。接着收敛起来的光,自然而然的自在悠游,不费丝毫气力,这就是「安神祖窍,翕聚先天」一节功法。接着,一切影响逐渐消失,进入寂然大定的状态,这就是「蛰藏气穴,众妙归根」的一节功法。这里是一节功法中具有三节,至于一节功法中具有九节,等到以后再向大家仔细解释。
现在先谈谈一节功法中具有三节的问题,当处于「涵养」阶段开始入静时,「翕聚」就是「涵养」,「蛰藏」也是「涵养」,到了「翕聚」阶段,「涵养」「蛰藏」都是「翕聚」,到了最后「涵养」、「翕聚」也就是「蛰藏」,中间一层还可以依此类推。不须要改变意念所守的部位(窍),而这部位自会分开;这就是所谓「无形之窍」,那怕部位有千处万处,也只是一处。不须要改变功法所立的阶段(时),而阶段自会分开,这就是所谓「无候之时」,那怕阶段分成元会运世(一世,为三十年;一运为十二世;一会为三十运;一元为十二会。),也只是一刻而已。
一般来说,心神不到极静阶段,它就是不能动;即使动,也是一种妄动,而不是本体的动。所以说:「心神因对事物有所感受而动,那是人性的欲望所驱使;而不因对事物有所感受而动的心,那才是天地之动。不要用天的『动』来对应天的『性』,这句话说的是个『欲』字。」欲望就在于有「物」。这就是《易经艮卦,象词》所反对的「出位」之思,是一种有「动」的动。如果能做到一念不起,于是正念就会产生;正念也就是「真意」。在这寂然大定之中,天机忽动,那不就是无念的动吗?所谓「无为而为」,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我那首律诗的头二句,已经全部概括了金华的作用。下面二句,意思是「日月互体」的意义,「六月」指离卦的火;「白雪飞」是指离卦中间一爻的真阴,将返归于坤()也。「三更」指坎卦的水;「日轮」指坎卦中间一爻的阳,将要赫然返归于干()。所谓「取坎填离」就包含在这两句诗当中。再下面二句,说的是斗柄作用,能够升降整个气机,「水中」岂不是坎卦吗?「巽风」指的就是眼睛,眼光照入坎宫(下丹田),吸引那太阳之精。「天上」指的就是干宫(头顶),「游归食坤德」,指神入气中,天入地中,须要温养神火。最后二句是指出诀中之诀,那诀中之诀,始终离不开所谓「洗心涤虑为沐浴」这句名言,请看孔学的精髓是从《大学》所讲的「知止」开始,到「止于至善」归结;也就是开始于无极,终归结于无极之义;佛学的精髓是以《金刚经》所讲的「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一大藏教旨;我们道学,则以老子所讲的「致虚极」来完成性命全功。总而言之儒释道三教不过是用一句话,来作为出死护生的神丹。那神丹又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要处无心」罢了,虽然我们道家功法中,最奥秘的就是这个「沐浴」,可是整个一部功法,不过用「心空」两个字就足以全部概括了之。现在我用这句简单的话点破玄机,省掉你们各位再费几十年功夫去参访了!
各位还不明白前面所讲的「一节中具有三节」的意义,现在我再以佛家的「空、假、中」三观作为例证,这三观当中,头一个是「空观」,就是叫你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空虚的;第二个就是「假观」,虽然你把一切事物都看成了空虚,但又不能把万物都毁掉,还要在这名为空虚的世界里建立一切事物;只是把它们看成虚假的而已。第三个就是「中观」,既不能把万物毁掉,又不对万物执着,保持若即若离的中路。当你在修头一个「空观」的时后,虽然已将万物看成空虚,但也知道它们不能毁掉,也知道不应当对它们执着,其实你是兼修「假观」和「中观」了。不过你毕竟还是以「看得空」为着力点。所以说,在修空观时,空当然是空观,假也是空观,中也是空观。依此类推,修假观时是在用字上下的力量居多,假当然是假观,但空也是假观,中也是假观。同理,在修中观时也把万物想成是空的,但不叫它空,而叫它中;也把万物看成是假的,但不叫它假,而叫它中;至于中,就更不用说,必然叫它中了。
我虽有时单独说离卦,有时也兼说离坎二卦,但中心意思究竟没有变动。我开口就提示过「枢机全在两眼」。所谓「枢机」指的是用。用这个来斡旋造化,不是说造化只有这一点点。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眼、耳、口、鼻七窍,全都是光明宝藏;难道我只知道取两个眼睛,而其它就一概不闻不问吗?不是,请看上面所讲的,用坎卦的一阳,还要用离卦的光去照摄,就可以明白。朱玄育先生曾经讲过:「瞎子不好修道,但聋子不碍事」。这与我说的有什么两样?我只不过特别强调一下谁是主,谁是辅,谁轻,谁重而已。
日和月原是一种物质,日中含真阴,其实日中之暗处,实际上是月的精华,所以「月窟」并不在月上,而在日上,所谓月之窟,应当叫月留的窟。不然的话,直接说月就行了,何必说「月窟」。月中含有真阳,其实月中之白处,就是日的光华;日光反照在月上,这叫作天给的根;不然的话,直接说天就行了,何必说「天根」。一个日,一个月,分开了只能看成是半边,合起来才是一个全体;这好比一夫一妇,个人独居,就不成家室;只在有夫有妇的情况下,那一家才算是完全。但是,用人间事物来比喻大道,是不完全妥贴的。因为夫妇二人分开,仍然是两个人体;而功法中的日月两者分开了,就不成全体了。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眼和耳也是一个整体。我说,瞎子已没有耳朵,聋子已没有眼睛了。这样看来,说甚么一件东西?两件东西?说甚么六根?六根其实就是一根。说甚么七窍?七窍其实就是一窍!我说的这些话,只是透露它们相通的地方,所以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你们各位却专门抓住那些间隔的地方,所以随时会掉换看法。
百日立基第九
吕祖说:心印经有说:「回风混合,百日功灵。」说明炼功要有一百天,才奠定基础,才有真光出现。比如说,各位回的光,目前还是一种眼光,不能说是神火,不能说是性光,更不能说是智能之烛光。等到回光一百天之后,精气自然充足,真阳自然生成,水中自然会产生真火,照这样实行下去,坎离自然会交媾,圣胎自然会凝结。我还在不识不知之中,那婴儿却已经发育生成了,整个过程完全是自然的;如果稍稍用意志来促进的话,那就不是正道,而是外道!
百日立基,不是硬性规定非一百天不可也;那就好比说:一日立基,并不是指一天;一息立基,也不是指一次呼吸。「息」这个字,是「自」、「心」两字组成的。自心为息,元神、元气、元精的升降离合,全由心来操纵;没有什么实和虚,全部都依靠意念。所谓「一念一生持」,何止是一百天?即使是一百天,也不过是一念而已。立基的一百天中,关键是要得力。白天得力,晚上受益;夜间得力,白天受益。「百日立基」本是玉皇的旨意。天上仙真说的话,没有一句不与人身相应;世上真师说的话,没有一句不与学道的人相应。这真是玄中之玄,很不容易理解的。只有到了见性阶段,你才会明白!所以学道的人必须求真师传授,尽管他是想到哪里,便说到哪里,但一句一句都有它的效验。
性光识回第十
吕祖说:回光功法,不论行住坐卧,都能够实行,并不拘于形式;但只要自己得机得窍。我在前面曾经提示过:「虚室生白」那句话,那光不就是白色吗?
但有句话要提醒大家,开始炼功,从未出现过光的时后,忽然虚室生白了,那就是炼功的效验。如果出现了光,而你的心意却去追随它,于是就落在意识界里去了,那光就不是本性之光了。所以你决不要去管它有光无光,只要无念生念。什么叫「无念」?就是佛家常说的「千修千处得。」什么叫「生念」?就是佛家常讲的「一念一生持」,这里指所生的意念,是一种正念,与平时的念头不同。「念」这个字是「今」「心」两字组成的念,今心为念,念,就是现在的心。这心也就是光,就是用来作炼丹的药。
一般人看外界的事物,随便举目用眼光一看,还来不及区别事物的特征和属性,这时的眼光还属于「性光」。就像镜子和静水一样,映照出各种影像,本是无心无意。过了一会儿,那眼光就成为识光了,因为它已经在区别事物的特征和属性了。镜子里有了影像,已经不是镜子了;静水里有了影像,已经不是静水了;光里面带有意识,还叫什么光呢?
各位在回光时,开始时是一种「性光」,转念之后就变成「识光」,因为意识一生起,光也就杳无踪影,无从寻觅。这并不是说没有了光,而是光已经转化成了识。黄帝说过:「声动不生声,而生响」,就是这个意思。《楞岩推勘入门》说:「不在尘,不在识,惟还根。」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尘」指的是外物,佛家称之为「器界」,与自我毫不相干。心如果去追逐外物,那就是把外物当作了自我。外物的属性,总归要返还给外物。比如说,通气是门窗的属性,但通气要还给门窗;明亮是日月的属性,但明亮要还给日月,硬要把它当作我,始终都不会为我所有。按照这个道理来推论,直到有一个属性不能返还给人了,这东西不是你的自我,又是什么呢?将明亮还给日月,但日月被你所看见过的那部分明亮,却不能返还。天空看不见日月的时候,人却没有见不到日月的感想。如果是这样,那么区别日月的属性,还可以为我所有吗?不知道根据明暗来区别的属性,当明和暗都忘掉的时候,那区别又何在?这里面也有着返还,那就是所谓「内尘」。只有达到「见性」的阶段,那才是没有返还。不过,在见性的阶段,「见」并不是真正的见,所以连「见性」也还给人家了。这里所返还的,是那种随意识念虑而流转的「见性」,也就是《楞严经》上释迦向弟子阿难所说的「使汝流转,心目为咎」。他阐述「八识」(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加上传送识和阿赖耶识)、「八还」时,前面七种识,都一一论证他们存在返还,但到了第八识,姑且留下这个「见性」不谈,当作阿难的柱杖。我们追究一下见性这回事,即然它带有「八识」,那就不是真的没有返还。如果连这个也给破掉了,那才是真正的见性,真正的没有返还了。
各位回光,正要回那最初没有返还的那种性光,所以一丝一毫意识念虑也用不着。牵引你意识念虑在流转的,就是那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但能使你成就菩提(正觉)的,也只有这六根,一切尘和识都用不上。这里,不是讲利用那六根本身,而是利用那六根中的属性。现在你如不想陷堕入识的困境,那么在回光时,必须利用那六根中本原之性;如果带着识去回光,那就是利用那六根中的识性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就在这个地方。
总而言之,用心用意就是识光,放下意念就是性光;这里头有毫厘千里之差,不可不去仔细地分辨。要知道识不断,神就不生;心不空,丹就不结。心静就成了丹,心空就成了药。不执着任何事物,叫作心静;不留恋任何事物,叫作心空。空,如果是能够发现的空,那空就不能算空;直到空得忘掉了空,这才算做是真空。
坎离交媾第十一
吕祖说:如果用卦象来解释功理,那么凡是漏泄精神,流动而接触外物的,都属于离卦;凡是收转神识,静定而涵养中心的,都属于坎卦。七窍中外走的是离卦;七窍内返的是坎卦。
离卦中间那一阴爻,以追逐颜色和声音为本职;坎卦中间那一阳爻,以收回听觉和视觉为本职。广义言之,坎离就是阴阳;阴阳就是性命,性命就是身心,身心就是神气。
学道的人,一开始收敛气息,他的精神就不再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流转。广义言之,就是已经真正的坎离相交了。何况沉默安静下来打坐,那当然更高一等了。
周天第十二
吕祖说:所谓周天,并不是以气为主体,而是以心到为妙诀。如果要问究竟怎样来实行周天,那就等于揠苗助长了。无心而守,无意而行,这就是周天的要领。
请大家仰望天空,那半球的天穹被人们划分为三百六十五度,日月星辰无时无刻,不在天球上变换位置,可是北极星这个斗枢,却终古不移。我们的心也是这样。那心好比斗枢,气好比群星,绕着斗枢在转。
我们身上的气,在四肢百骸当中,原是贯通着的,炼功时也不要十分用力。只要利用这血肉之躯,锻炼好识神,断除了妄见,炼丹的药于是就会产生。那药,并不是什么有形之物,而是性光;也就是先天的真气。他必须在寂然大定以后才会出现。这种药并没有什么采法,侈谈什么采法的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持久也出现了真气,心地一片光明,自然会达到心空尘漏的境界,于是就能从尘海中解脱出来。如果你今天大谈「龙虎」,明天大谈「水火」,把功理挂在嘴里,不去实践,最终只能成为妄想,我从前亲受火龙真人(郑思远)的口诀,讲的就是这样。不知现在的养生丹书上是怎么说?
一天有一次周天,一刻也有一次周天。坎离相交之处,就是一周。我身中的坎离相交,也相当于天穹的不停回旋。但是有相交之时,也就有不交之时。而天穹的回旋,却没有一刻停止过。如果能做到那样的阴阳交泰,达到大地阳和;这时,我的中宫居于正位,万物随着一时畅遂,这就是养生经典中所提的「沐浴法」。那不是大周天又是什么?
这里头的火候,实实在在有大小的不同;但认真说来,却又没有大小之分别。等到你功夫纯熟自然,也不知到坎离是什么东西!天地是什么类别!什么叫相交?什么叫一周叫两周?又从何处去找那大与小的分别呢。
总之,身中的回旋运行,很难达到「真」的地步,不真,虽然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还是很小;而真,身内一回旋,天地万物一齐跟着回旋;即使在一方寸的地方运行,当然是很小了,实际上却是极大。所以,金丹的火候,全要尊循「自然」二字;不自然,天地还是那个天地,万物还是各自的万物,如果想硬行让它们揉合在一起,却始终也合不起来。比如天气干旱,阴阳不合,但天穹中的乾坤运行,未尝不按周天规律在运转;不过始终觉得有许多不自然的地方。如果我们能转运阴阳,调和自然,云满天空,甘霖下降,草木都得到了充分湿润,山河也随之运行流畅,这时,即使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也就觉得很快烟消云散,这就是大周天的原理。
有人问:活子时本来很妙。可是你说必须先认定正子时,这不是着相了吗?
答复是:不着相,如果不指明正子时,又怎样来认识活子时?既然认识了活子时,毕竟还有那正子时的存在,它们是一是二,非正非活,总归要人们看得真切才行,看得真,就没有不正,没有不活了。如果看得不真,能弄清楚哪个是活?哪个是正吗?提到活子时,那是时时都可能出现的,但在半夜那个正子时里,人的意气毕竟清明一些,活子时就显得更加容易出现。如果没有发现过活子时,暂且可以在正的时候去等待、去求取;当正子时显到来时,那活子时也无不显其神妙了。
劝世歌第十三
吕祖《劝世歌》(释文)是:
我因度世心肠热,不惜苦口婆心在饶舌。
如来佛也为了大因缘,直指生死真是可惜;
老君说懮患由于有身,传示谷神但人不识。
我现在讲讲求真之路,《易经》上有句「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就是玄关,子午中间可以定息。
光回到祖窍万神安,药产在川原一气出;
透过帏幕度化出金光,一轮红日经常耀日。
世人把它错认为坎离精,搬运心肾反而违隔;
不如用人道来合天心,天若符合道自符合。
放下万缘丝毫不起,这是先天的真正无极;
太虚穆穆没有征兆,性命关头忘了意识。
意识忘后见了本真,水清珠现玄妙难测。
无始的烦恼一旦空,玉清宫降下九龙册。
升上云霄汉登上天阙,掌握风云驱赶霹雳。
总之,凝神定息是起点,退藏到密地达到常寂。
我从前引度张珍奴时,曾给她写过两首词,其中含有功法宗旨。
「道无巧妙,与妳方儿一个;子后午前定息坐,夹脊双观昆仑过。这时得气力,思量我。」
「坎离震兑分子午,须认取自家宗祖。地雷震动山头雨,带洗濯黄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闭固,炼甲庚要生龙虎。待他问汝甚人传?但说道先生姓吕。」
词里的「子后午前」,不是指时间,而是指坎离。「定息」,就是息息归根于中黄部位。「坐」,指的是心不动。「夹脊」,不仅是指背上轮子,而且是直通玉京的大道。「双关」,这里不大好解释。炼功时要避免忘神而守,而要注重虚极和无所守。按这样的原则去守,液于是会转化,血于是会生成,最后就会返归于先天,达到气归于神,神还于虚,虚合于道,道圆于志,志满于愿。口诀真是说不完的,这里就是个例子。至于「地雷震动山头雨」,说的是真气生成。「黄芽出土」,说着是真药生成,而它们的基础,都建筑在神守双关上。短短两首词,已经把修行的大路概括完了。读懂了它,对于别人随便侈谈的理论,你就不致被他迷惑了。
从前孔子和颜回一同登上泰山顶峰,望见山下东吴地界有一匹奔驰的白马。颜回说:「看见那白马奔跑的轨迹,就好象一匹白布」。唉!他也太浪费眼力啦!结果走落了神光,所以他会过早的夭折。大家练习回光功法,可要注意啊!
回光全在专心一志去实行。只须将真息凝照于中宫,久而久之,自然通灵达变。总之,要以心静气定为基础,心忘气凝为效验,气静心空为丹成,心气合一为温养,明心见性为了道。
各位最好分头去认真实行,错过了光阴,那就太可惜了。一天的时间不回光,那一天就做了鬼,一息的功夫能回光,那一息就成了仙,悟道参禅,脱胎换骨,就从这里开始,各位要勉力啊! 本文链接:https://www.liumenghao.com/guoxue/4107.html
-
本文标签:太乙金华宗旨原文及译文 太乙金华宗旨 太乙金华宗旨txt下载 太乙金华宗旨pdf下载 太乙金华宗旨原文 太乙金华宗旨简介
ID:liu_menghao
太乙金华宗旨原文及译文
39384 人参与 2022年02月12日 15:52 分类 : 国学大师_国学经典_国学教育_国学经典名句 评论
- 2022-02-12 15:57《太乙金华宗旨》,在国外的传奇经历
- 2022-02-12 16:02《太乙金华宗旨》道光辛卯版
- 2022-02-12 16:10 太乙金华宗旨——泥丸宫 → 松果体
- 2022-02-12 16:03《太乙金华宗旨》原版王重阳著